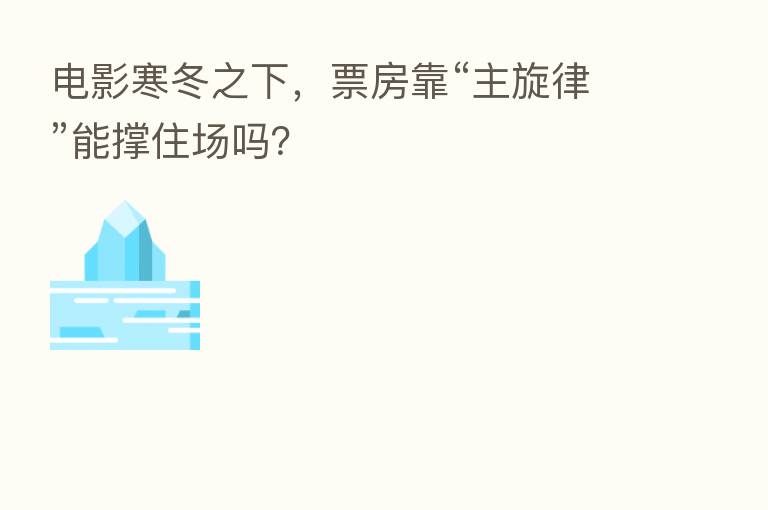
主旋律“进阶”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徐鹏远
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,“主旋律电影”成为了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,就连金爵电影论坛的日程中,也专门安排了一场以“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”为主题的讨论。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,上影节一直被视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晴雨表。因此,这届影展对主旋律的高度关注,一定程度上表露着行业对于自身发展进路的某种共识,或者至少是对现实境况的一次及时反映与总结。
2020年,全球电影产业都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,据年末发布的《电影蓝皮书: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(2020)》预计,全球影院票房需要五年时间才有望恢复至2019年的市场规模。中国电影当然也无可幸免,经历过179天的院线停摆,2020年的全部票房仅203.14亿,直接回落到了2013年前的水平。但不幸之中也有奇迹。同样在这一年,中国电影凭借《八佰》首次登顶全球票房宝座,其中仅《八佰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金刚川》三部作品就贡献了近35%的份额,《八佰》更是以31.11亿元的成绩成为了全球年度票房冠军。
这一势态在随后依然延续着。2021年,中国电影蝉联全球票房 一,超过10亿的11部影片中,有4部是主旋律作品,《长津湖》57.75亿的票房还打破了32项影史纪录。进入2022年,元旦和春节两个重点档期,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和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各自档期的领跑者;3月以来,对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的防控让电影市场再次跌入冰点,全国一半以上的影院暂停营业,仅有3部影片的票房超过1亿——排片比例逐渐下调的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仍然稳居首位。
在电影产业元气大伤的至暗时刻,主旋律作品不仅以出众的市场结果证明了其强大的号召力,更挽住了属于中国电影的一线生机。在这个意义上,那场上影节论坛中关于“主旋律电影就是新主流电影”的讨论,远未结束。
主旋律电影的进阶
对于中国电影而言,主旋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。1949年后,中国电影承载了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功能,同时在“统购包销”的管理政策和经营模式下,全面呈现着浓重的“主旋律”性质。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电影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市场滑坡,于是各大制片厂纷纷转向所谓的“娱乐片”,到80年代中期,“娱乐片”产量已超过当时年均总产量的50%。鉴于此,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,明确提出了“突出重点、坚持多样”、坚持“文艺的主旋律”的要求,这一精神随后被总结为 “突出主旋律,坚持多样化”,并 终在1990年正式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指导方针。90年代,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,主旋律创作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和强调。
但正因如此,主旋律的概念也长期处于一种刻板的状态。事实上,主旋律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。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就认为,主旋律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:“一种理解是,主旋律是带有价值导向和思想导向的这样一种电影;另一种指向是,它是携带着真善美正能量大制作的电影; 三种就是只突出价值宣传,所谓正能量、制作规模不在它的考量范围之内。”而从主旋律提出的具体背景来看,也只是与“娱乐片”相对应的一种导向,并不涉及明确的题材范围和创作模式。然而由于固有认知的影响,大众层面对主旋律的理解往往直接指向革命历史题材,就连行业内部,也在一段时间里习惯性地将其与献礼片、任务片画等号。尤其从1994年起,进口分账片对国产电影持续造成的压力和影响,更让主旋律在初步形成的电影消费中,走向了“非市场化”的路径。
2002年,伴随新的电影管理体制开始实施,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时代拉开了帷幕。主旋律电影在逐渐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中,也很快迎来了新的起点。2009年,一部《建国大业》横空出世,172位明星参演的空前阵容带来了充足的话题性和市场卖点,4.2亿的票房领跑了当年度国产电影,成为仅次于《2012》和《变形金刚2》两部好莱坞巨制的票房季军。与此同时,《风声》《南京!南京!》与内地香港合拍片《十月围城》三部主旋律作品也跻身到了票房十强的行列。这是主旋律电影 一次集体性地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商业价值,为主旋律的市场化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2011年,《建党伟业》沿袭全明星模式,再次拿下超过4亿的票房,位列当年 七。
不过,这几部电影仍旧属于依托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、建党九十周年基础上的献礼作品,尤其像《建国大业》和《建党伟业》,无论拍摄、宣传还是排片,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。2013年的《中国合伙人》、2014年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和2016年的《湄公河行动》,则完全脱离了重要历史节点的辅助,并开始以民营公司为主导,更纯粹地开拓着主旋律电影的商业版图。 值得珍视的是,陈可辛、徐克、林超贤三位来自香港的导演,还将香港电影的成熟经验融入了这一题材的创作,做出了主旋律作品类型化的关键探索。
版权声明:本文为原创文章,版权归 头条123 所有,欢迎 本文,转载请保留出处!

 微博月活跃用户达4.46亿 同比净增长7000万
微博月活跃用户达4.46亿 同比净增长7000万 创业板公司融资余额减少4.56亿元,22股遭减仓超5%
创业板公司融资余额减少4.56亿元,22股遭减仓超5% 新能源行业上半年过得如何?电池厂回暖、整车厂“连汤都喝不到” | 2022中报盘点
新能源行业上半年过得如何?电池厂回暖、整车厂“连汤都喝不到” | 2022中报盘点 写大人童心未泯的句子
写大人童心未泯的句子 同方股份:公开转让同方全球人寿 有限公司股权
同方股份:公开转让同方全球人寿 有限公司股权 斩获亚军!西人马赢得 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亚军并斩获金奖!
斩获亚军!西人马赢得 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亚军并斩获金奖! 单利和复利的区别是什么,单利和复利的区别具体介绍
单利和复利的区别是什么,单利和复利的区别具体介绍 努比亚 Z40 系列预热:2 月发布
努比亚 Z40 系列预热:2 月发布 广东省终端快充行业协会正式成立:成员包括信
广东省终端快充行业协会正式成立:成员包括信 股票估值高低怎么看,股票估值高低有什么意义
股票估值高低怎么看,股票估值高低有什么意义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:游戏化教学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
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:游戏化教学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十四五规划新机遇,电小二户外电源助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
十四五规划新机遇,电小二户外电源助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 坚持合规导向,中银消费金融践行普惠金融
坚持合规导向,中银消费金融践行普惠金融 11家创新层川企“中考”成绩出炉:10家盈利1家亏损 欧康医药拟登陆北交所 领航科技又亏
11家创新层川企“中考”成绩出炉:10家盈利1家亏损 欧康医药拟登陆北交所 领航科技又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:全国现有5.9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:全国现有5.9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小米 12 真机曝光:镜头模组搭配线条设计,绿、
小米 12 真机曝光:镜头模组搭配线条设计,绿、 上海 三批集中供地:保利发展联合体36亿元竞得徐汇龙华住宅地块
上海 三批集中供地:保利发展联合体36亿元竞得徐汇龙华住宅地块 安卓江湖修炼指南:有了它分分钟让程序猿逆袭
安卓江湖修炼指南:有了它分分钟让程序猿逆袭 首个社区版本!OpenCloudOS 8.5 正式发布:稳定的企
首个社区版本!OpenCloudOS 8.5 正式发布:稳定的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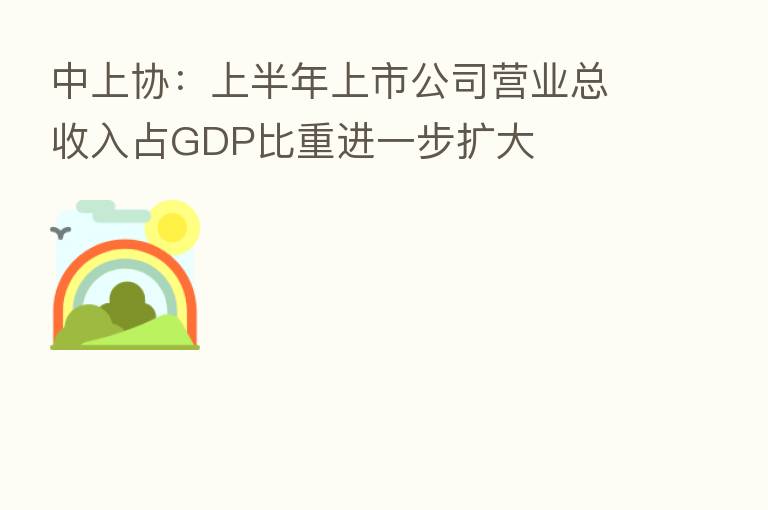 中上协:上半年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
中上协:上半年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